文:孟宗
「永續發展是符合今日需求的同時,不會干擾到未來世代追求它們自身需求的發展方式。」
– Gro Harlem Brundtland, 1987
在熟悉的風景中見到陌生的事物,常常是行動的開端。在舊金山區的南灣有一座濱海山丘,上面矗立了一群大大小小的木製巨柱,幾座隆起的小土丘,入口不遠的斜坡上有兩排水泥護欄排成箭頭的形狀。另外有一處鐵架,懸掛的鋼管會隨風擺動。山坡上長滿了原生草種,除此之外別無他物。看到這些地上的謎題,彷彿是原住民留給後世的遐想,也促使人沿著高低蜿蜒的步道繞行。這座畢克斯比公園(Byxbee Landfill Park)位於矽谷中心的保羅奧圖市北側,隔著208號快速道路和史丹佛大學遙遙相望。公園是保羅奧圖海灣保育區(The Palo Alto Baylands Preserve)的一部分。原本是面積150英畝(60公頃)的垃圾場,由設計師哈葛瑞夫(George Hargreaves)於1991年完工。

畢克斯比公園(Byxbee Park, Palo Alto. 攝影:蘇孟宗,2010)

畢克斯比公園(Byxbee Park, Palo Alto. 攝影:蘇孟宗,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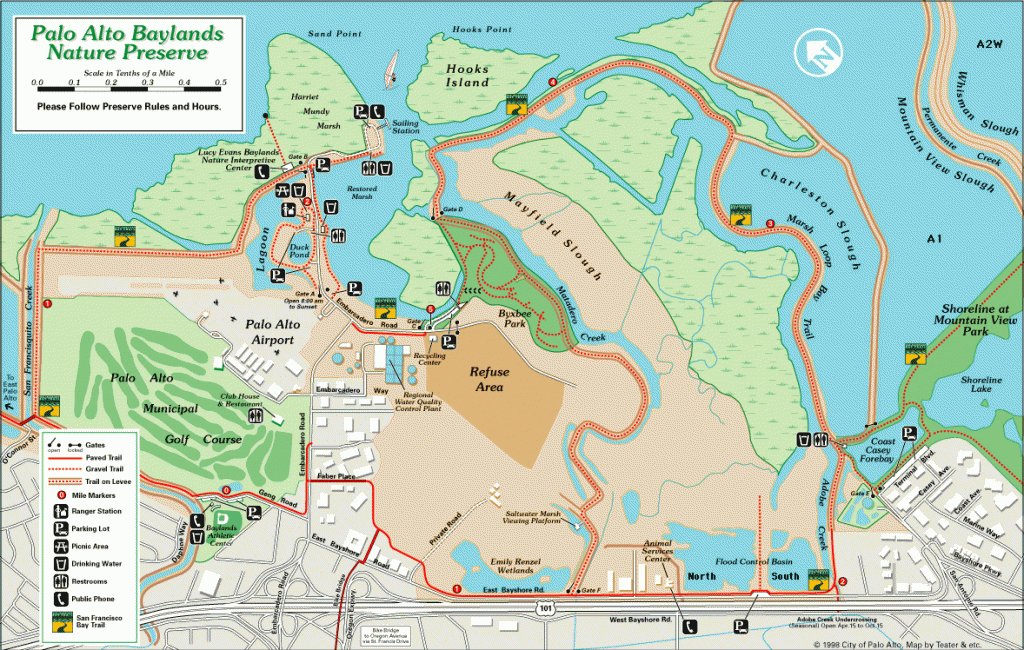
保羅奧圖海灣自然保護區全圖(Palo Alto Bayland Nature Preserves)
(圖片來源:http://www.mappery.com/map-of/Palo-Alto-Baylands-Nature-Preserve-Map)
在新舊併陳的體驗中,會產生不一樣的認知,進而對於周圍的物種和棲地建立起新的理解和移情作用。以畢克斯比公園為例,由市政府經由公共藝術計劃和幾位藝術家理查(Peter Richard)和歐本海默(Michael Oppenheimer)合作,以七十二隻廢棄木製電線桿設置了立柱場(Pole Field),由於電桿的高矮不一,整個陣列的頂端隱約構成一個傾斜面。排成為箭頭形狀的水泥護欄指向附近的輕航機機場,成為起降的可見標示。因為垃圾產生的沼氣也有一座燃燒甲烷的裝置設置在鑰匙孔形狀的卵石床上。山坡的另一面由幾條混凝土組成的堤堰,配合草溝的設置防止坡面侵蝕。山脊上的數座小土堆,則暗示著海岸原住民曾經留下的土丘。之後至今已經超過二十年後,即使2013年部分地區土丘部分毀損,仍然受到地方居民的喜愛,無論是慢跑、單車、或者單純的賞景。
這樣人類與自然的碰撞,也在金門大橋底下的「克里斯原野」(Crissy Field)見到。因為潮汐漲落的緣故,哈葛瑞夫在昔日作為軍事堡壘的普西迪公園(Presidio Park)北側海岸保留了大片的草坪,相隔一個三米寬的步道,即是沙灘與濕地。克里斯原野儼然已經成為觀看金門大橋的最佳景點,由金門大橋的遊客中心往下走,穿越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堡壘隧道之後回首觀看,朱紅色的鋼骨懸吊橋樑便盡收眼底。在這片稱為「原野」(field)的草坪上空無一物,呼應了洪泛時期的安全性,留白的空間也開放成為機能的最大化,也避免和附近近乎飽滿的眾多歷史文化景點爭奇鬥豔。再往東側行走則是沼澤地,由低矮的混凝土矮牆兼座椅匡定人類與自然的邊界,也提供了駐足觀賞的臨界空間。隱藏在這裡的,是觀光勝地與財務金融的城市中的自然桃花源,引人深思的卻不是精心構圖的風景畫,而是原始生命力與人類文明的撞擊力量。稍微可以想見所謂的「金門」(Golden Gate)作為沙加緬度河和聖瓦金河所形成的三角洲和出海口,在人類到來之前的本來樣貌。

克里斯原野(Crissy Field, San Francisco)(攝影:蘇孟宗,2018)

克里斯原野(Crissy Field, San Francisco)(攝影:蘇孟宗,2018)
另外在紐約曼哈頓半島的西側水岸的街廓中,有四座公寓大樓圍成一座小型的鄰里公園和兒童遊戲場,進入之後有一面超過八公尺高的巨大石牆,矗立在入口不遠的公園中央。這面石牆介於草地區和兒童遊戲場之間,上一片一片的岩板重疊之後扭曲,好像受到地層擠壓之後露出地表,這樣的東西出現在城市中,立在面積不到一公傾的綠地中顯得格格不入。石牆界定出的是公園的邊界,往西走是由綠樹、步道、溜滑梯和沙坑圍塑成的一片兒童遊戲天地,東側則是草地和突起的山丘。石牆上方會有細小的水流流出,冬天的時候雪水會凍結停留在石牆上,滴落下來的時候結成懸掛的冰柱,這是凡佛肯堡(Michael Van Valkenburgh)於2004年所完成的淚珠公園(Teardrop Park)。
位於都市地區的小型淚珠公園,則採取誇大、想像的策略。在周邊30層樓高的住宅環繞下,日照稀少、植物也難以生存的狀況中,設計師凡佛肯堡和藝術家漢摩頓(Ann Hamilton)以及莫西爾(Michael Mercil)合作,借用基地以外的特徵與想像,也就是紐約地區的地質與自然循環,憑空創造新的環境體驗。訪客進入公園之後所面對的一堵巨大石牆,以及步道旁豎立擠壓的石板,實際上是參考十九世紀哈德遜畫派畫家如杜蘭(Asher Durand)的風景畫,再經由經由電腦繪製和精密的施工過程所生產。沿著這道石牆,才由一處狹窄的甬道進入核心的兒童遊戲場裡面。荷蘭地景學者德榮(Erik de Jong)評論這座公園時候以正面的語氣說「那裡沒有那裡」(there is no “there” there),因為訪者在空間中不斷受到空間和物件的推擠,而自然行進到下一個空間。

淚珠公園 Teardrop Park, New York (攝影:蘇孟宗,2014)

淚珠公園 Teardrop Park, New York (攝影:蘇孟宗,2014)

淚珠公園基地平面(Teardrop Park, New York. Site Plan.)
在這些不期而遇的景觀設計中,我們可以找到「永續之美」的線索。較之於1970年代的景觀建築界在生態科學和設計藝術之間出現的一道鴻溝,1980年代哈葛瑞夫和凡佛肯堡這一代的地景建築師開始研究或開業的時候,便存在著兩種典範。第一類是生態設計,起源於賓州大學的伊恩・瑪哈(Ian McHarg)等教育家的寫作和教育。這個模型對設計程序的主要貢獻在於以更紮實、更科學的方法來組構概念產生之前的設計階段。第二個模型是地景建築的藝術觀(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art),源自於哈佛大學彼得・渥克(Peter Walker)等教育家的教學和實踐。他們擔心設計程序過分受到生態、社會和行為等各種分析的牽絆,以致於使得地景淪落為機能的從屬。將景觀設計視為藝術的主要貢獻,是在於概念形成和設計發展的階段,能夠把當代藝術的語彙和策略應用到地景的創造上。
自然的設計和保育,最後還是關係到人類的社會與文化。傳統的風景美是一種疏離的審美概念,由遠處觀看。對於視覺景觀的過分強調,也忽略了對於生態(自然)和人類(文化)的關懷。如果回到現代景觀建築或景觀設計的故事開端,當規劃師在都市中設置都市公園,強調城鎮與鄉村的對比,希望緩和工業化的衝擊的時候,就已經重新定義了都市中(人造)的自然美這件事情。歐姆斯德在1868年〈展望公園科學協會〉演說開啟了風景美學的在地化,他並沒有移植英國的文人風景美學論述,而是回溯自己與弟弟在野地露營的經驗,以選擇紮營地點的原則。他認為公園是藝術品,為了產生某種心理效應而設計。因而公園不只是「都市之肺」的空氣清淨機,或是提高生物棲息地的避難所,也是一種特別的文化機構,進行社會化功能的社交場所。
環境保育到人文關懷的並重,也是永續性(sustainability)這個概念提出時候的意義。1987年由聯合國委託,以挪威前總理布倫蘭特(Gro Harlem Brundtland)為首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提出的布倫特蘭報告(Brundtland Report)中提出,「永續發展是符合今日需求的同時,不會干擾到未來世代追求它們自身需求的發展方式。」依循這份報告的原則,在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辦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簡稱地球高峰會 (1992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ka. the Earth Summit, in Rio de Janeiro) 。這次地球高峰會簽署了下列文件︰〈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生物多樣性公約〉、〈森林原則〉、〈联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约〉。在其中與景觀設計相關者,主要為關於「人類的角色」的第一條原則,主張「人類處在關注持續發展的中心。他們有權同大自然協調一致從事健康的、創造財富的生活。」關於「發展權」的第三條原則,則指出「發展權必須得到履行公平地滿足當代人和後代人的發展和環境需要。」第四條原則則是關係到「環境保護的發展進程」,其中表示「為了實現永續發展,環境保護應構成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的發展進程,不能孤立地考慮它。」

布倫蘭特(Gro Harlem Brundtland,挪威前總理,「永續之母」與唐獎第一屆「永續發展獎」得獎人)
1987年攝於里約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 (圖片來源:UN Photo/Greg Kinch.)
永續性強調的是環境保育、社會正義和經濟發展三者並重的論述,也是「後地球日」(Post-earth day)的年代下,環境主義由保護和保育轉變為永續發展的關鍵。然而每個人聽到「永續」的時候,反應都不太一樣。地景建築學者麥爾(Elizabeth Meyer)早年關注如何把環境價值轉譯為設計形式,在2008年的〈永續美感:外表的展演〉一文,可說是她在生態設計美學研究上的集大成之作。文中首先提出,一般人(包括許多景觀設計師)面對「永續」這個詞彙的時候,態度約可以分為四種態度:(1)「打呵欠:承認+維持原樣」(Yawn: acknowledge + continue on):聽到「永續」就「打呵欠」的人,會承認其重要性,然後繼續眼前的工作。他們會覺得:「永續設計就是我們的工作,那有什麼大不了?」;(2)「擁抱:採納+傳福音」(Embrace: adapt + proselytize):「擁抱」永續性的人則認為,我們必須適應新的理想,同時必須懺悔改信。但是這類的人時常會把「永續性」和「生態技術」劃上等號;(3)「驅散:避免+毀謗」(Dismiss: avoid + denigrate):「驅趕」永續性相關議題的人,會逃避並詆毀它的必要性。對他們來說,「永續性」等於「沒有設計」,也就是醜陋;(4)「藐視:私下採用+公開保持距離」(Distain: adopt in private + distance in public)。對於永續性抱持「藐視」態度的人認為,永續發展只能意會不可言傳,它是某種化約後的生態機能主義。
在永續性的普遍關懷之下,美學經常受到忽視,卻是最重要的。廣義來說,美學關係到的是日常生活的感受與昇華,卻因為藝術機構的專門化而遠離群眾。但是在永續性的大旗之下,美學是可以環境與永續思想中的重要推力。文學評論家布威爾(Lawrence Buell)於《瀕危世界的寫作》(Buell in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中表示,美國的環境政策缺乏「連貫一致的共同環境利益視野,不足以產生足夠的說服力來獲得公共支持」,他主張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政策或技術,而是「態度、感覺、意象、敘事。」基於這些原因,麥爾主張面對永續性的另一種態度,是將永續性(sustainability)這個名詞轉為「維生」(sustaining)這個動詞,「永續之美」(sustaining beauty)。她說道:
我將美學重新置入永續性的討論中。地景設計的外表,不僅僅是視覺、風格或裝飾議題(後衛的形式關切)。我試圖拯救視覺,作法是把視覺和身體的、多感的體驗作連結。我將解釋融入的美學體驗,可以導向我們對於環境的認同、移情、愛、尊敬和關心。
… 在這裡,我指的不只是圖畫風景和愉快、理想化的田園景致。我想提的是地方的體感感官經驗,導致新的意識的節奏和周期維持和再生的生命所必需的。這些地景有賴於(我們能夠)立刻體認、理解到地景的空間和形式中新的、不預期的形式、空間和序列、同時勾起的先前記憶和概念。
麥爾提出「永續之美」的命題,在其中顯示了文化和自然的交纏。看起來自然的設計,實際上卻容易隱形不可見,也間接造成了對於自然的忽視。所謂的仿生或是生態模擬,雖然是永續景觀設計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模仿自然的「過程」比起其外型更為重要。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維持必須藉由地景媒介」(Sustaining culture through landscapes),所以永續景觀設計與生態設計或復育生態學或保育生物學不同,也不只是追求生態績效(ecological performance)。於是麥爾認為:「持久的美麗是有韌性和再生的」(Enduring beauty is resilient and regenerative.),「古老過時的景觀美學概念仍然普遍存在,這樣觀念下的風景是通用、平衡、順暢、有邊界、迷人、愉快與和諧。我們必須透過新的生態學典範來重新審視。」這裡的「新典範」指的是由平衡與極盛相的傳統模式,轉變到將『干擾』(disturbance)視為正常的生態學模式。終究來說,地景設計促成了游移不定的體驗與觀看方式,「設計地景的經驗可以是注意力,漫遊和好奇,以及關心環境的空間實踐。景觀的經驗可以是一種學習和灌輸價值的模式。」
是否我們在景觀設計領域中談論美學,只會將這個行業貶低為無關緊要的綠化美化?許多符合社會正義或是生態原則的場所,看起來不一定符合我們期待中約定成俗的「美」。事實上,景觀設計的文化面向,其重要性不亞於生態面向與社會面向。無論是哈葛瑞夫的畢克斯比公園,或是佛肯堡的淚珠公園都重新定義「後工業時期」的崇高與壯麗,進而能夠引發環境的冥思,以及環境倫理所必須的行動和實踐。這樣的感動,類似於文化史學者史蓋芮(Elaine Scarry)在《論美與公正》(On Beauty and Being Just)書中提出來美感概念:「每當我們看到美麗事物的時候,我們會經歷到某種根本的『去除中心』(decentering)。『美』要求我們放棄我們自己作為世界的中心的想像位置. . . 這種轉變發生在我們感官的最根本處,發生在感官印象和心理印象的即刻接受。」風景美學是為了引發特定的情緒,究竟是因為外觀,抑或相對應的內心情緒,或許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改變我們對於「美」的概念。這樣的美感不會是靜態的、只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風景,而是與身體經驗結合,引發同情與想像的「永續之美」。
延伸閱讀
- Elizabeth K. Meyer, “Sustaining beauty. The performance of appearance—A manifesto in three parts,” in Journa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Vol. 3, Iss. 1. (2008), 6-23.
- George Hargreaves and Julia Czerniak, Hargreaves: The Alchem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ames & Hudson, 2009).
- Anita Berrizbeitia ed., Michael Van Valkenburgh Associates: Reconstructing Urban Landscap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atthew Morse Booker, Down by the Bay: San Francisco’s History Between the Tid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部分原文刊於 2017年八月號《綠建築》雜誌
學生、老師、父親,期望播種與收割的遊牧民族,修過建築史,教過景觀史,做過景觀設計和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