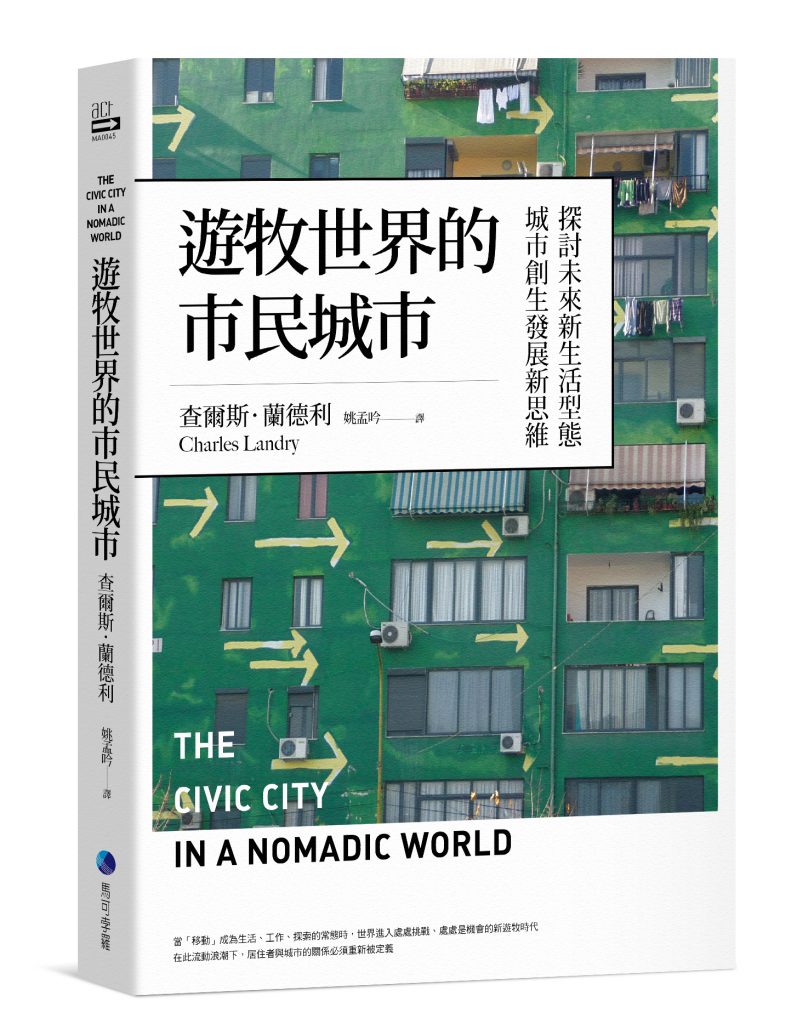文:查爾斯・蘭德利 Charles Landry
編註:
本篇文章選錄至《遊牧世界的市民城市:探討未來新生活型態城市創生發展新思維》一書;本書由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序曲
我們生活在尷尬的年代,因世界正轉向它的黑暗面,其時代精神是不斷上升的焦慮感。灰色地帶消失,我們的世界裡出現極深的斷層。我們的社會、部落本性及群體內外的本能都處於緊繃狀態,而我們的世界持續萎縮,城市變得更混雜、更遊牧且更多元。我們之間有更多人為了工作、休閒、愛情或探索而四處遊走,也因此深受來自其他地方想法和趨勢的影響。有些人認為這太超過了,必須停止,但有些人則因有機會成為更大世界的一部分而興奮不已。樂觀和悲觀者仍是參半的。
《遊牧世界的市民城市》有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就是開啟一個關於不同城市文明承諾的對話。這是一個城市定居公民和外地人─通常是臨時居民,聚集在一起形塑和創造一個他們都能參與的最好地方。這是世界日益鬆動、人民大量流動時代的核心挑戰。城市需要一個全面、積極的文本,把所有的人與其生活的地方綁在一起,讓日常的行為與活動和公民生活緊密相連。
在今日的語言裡,「公民(civic)」或「成為公民的(being civic)」只表示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與你的城市發生關係,而且住在城市裡的每個人都應享有這個機會。公民參與,包括參與城市運轉的機制,所以成為一個積極的公民並不困難。而成為「公民的」則需要尊重,讓跨越差異的對話與討論不會成為無盡的爭執。相對於這樣的交流禮貌,近年來的辯論已經變得粗俗了。一個偉大的市民城市,提供了文明的空間,因為這也代表不可剝奪的權利和自由。這讓我們在約束內(大家認同的行為規範)得以相對自由的行事,並且不受阻礙地參與政治、自願服務或其他我們想從事的活動。這讓許多城市保有新鮮感。不過,這在超過一百個國家是完全不可能的。自掃門前雪和集體性努力,這兩者間的創造性拉鋸,是城市創造(city making)的生命線。
凝聚力和人際關係是人類的核心特徵,問題是「和誰?」及「怎麼開始?」。人們常常有一種欲望,想連結不同的人、奇特的人、外地人或其他類別的人。這滿足我們探索的本能─一種求生的必要機制。不過,我們也追求熟悉的、已知的、可預測及穩定的狀態。因此,人們也會找尋並選擇志趣相投的夥伴。所以一切的開端,取決於我們與自己和環境共處的自在程度。不確定性會把人們和地方推向他們的部落本能及成見。政客利用這點,在「他們」和「我們」或「愛國者(可靠的好人)」和「全球主義者(令人困惑且不值得信任的壞人)」之間,狂熱地製造不安的差異,好像你不能同時擁有兩個身分。這令人聯想到當「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被視為骯髒字眼的黑暗年代。煽動者提出這個分野,像是宣告混沌和秩序的宇宙戰爭就要開戰。他們滿足了人們追求安逸和單純生活所需的秩序機制與敘事結構。這安定了他們的心靈,更穩固了某種心態,還提供了一張可以愉快地說服自己的精神地圖與腳本。簡單的比喻,如好或壞就能幫助判斷。而這樣的困境,是二十一世紀遭遇的最大斷層和衝突。
我們面臨一個嚴峻的選擇:封閉我們的世界,或是打開它?這不是一個簡單或二擇一的問題。它有很多複雜面。當全球的事物都無法分割地交織在一起時,封閉顯然是愚蠢的。其預設立場應該更接近開放而非封閉、更多同理心或同情心而非敵意,這並非我們不切實際,而是因為我們頭腦冷靜且務實。這歸結於我對城市、鄉鎮和村莊長期抱持的好奇心與觀察,以及居住的經驗。在此,我試圖以字面和影像來述說當代城市的趣味和不滿,並希望這個故事能觸動人們的共鳴。

下一步:公民的創造力
我們需要大幅度地轉移焦點。1990 年代末期我提出的「公民創造力」(civic creativity)概念,應該是引導城市進步的的核心題目。創造力不該僅限於科學或創意經濟的領域 ─ 例如網頁設計或藝術,都是很重要的。
我引述:
「公民創造力」被定義為應用於公益目的,富創造力的問題解決方式。其目的是對影響公共領域的問題持續產出創新的解決方案。「公民創造力」是公職人員、大小企業或民間社團組織共同有效運用他們才能的能力……這個議題旨在成為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和指導原則。
「公民」、「公共利害」或「公共利益」的概念,在過去的十幾年連續遭受抨擊。一連串與它們相關的負面字眼:值得的、阻礙事物、官樣文章、政治正確、效能低下、社會福利主義者⋯⋯脫口而出。「私人」(private)相對的被視為警覺、捷足先登、反應靈敏、管理良好,不同於自私或漠不關心。「公民創造力」企圖帶動最佳的公共服務、私人發起和市民行動主義,因為根據不同的狀況,每個人都有能付出的部分,試圖去除阻礙機會的守門人(gatekeepers)。但這只有當城市具更大議定目標去達成時才可能發生。
仔細檢視城市的願景宣言、策略和計畫,就會發現類似的想法一再出現,例如永續性、受良好教育和競爭力。但要如何達成?舊的模式還能運作嗎?二十年來,我們對社會、公民和以公眾為名的創造力需求較以往更為迫切。環境已然變遷,我們的用語可能不同,但大部分問題仍然維持不變,例如城市生活如何在個人與群體層面上變得更加充實,這就密切關聯到公平、機會、參與能力及市民慷慨程度等問題。
城市生活的緊迫問題也影響到公共領域:如何以文明、寬容的方式對待彼此以感到安全;或是既有的環境如何能激勵或打擊我們。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城市是否不公義與冷漠。許多解決方案需要從新的獎勵形態來創造,好讓大眾運輸變得更永續,以回應士紳化的壓力及其他種種。因此,社會創新運動脫穎而出。英國經濟學者周若剛(Geoff Mulgan)清晰地描述,「以社會為他們目的與手段的創新」或「同時滿足社會需求的新想法、產品、服務或模式,並創造了新的社會關係和合作⋯⋯它們是對社會有益的創新,又同時強化了社會的行動能力」(《社會創新的公開書》〔Open Book of Social Innovation〕)。哥倫比亞的麥德林曾是世界的謀殺首都,在經過創新方案的施行後,已經改變了其社會生活,像是連接一連串的電扶梯把你帶到有一萬兩千人口、過去很難抵達的貧民窟:十三號公社(Comuna 13)。或是它精心設計的西班牙公園圖書館(Parque Biblioteca España),激勵民眾學習。
這就是「公民創造力」的領域。它從中交涉,試圖平衡所有都市發展會涉及的各項利益衝突,即便政府當局可能擔憂自己會失去掌控權,因此總是牽涉到某種政治形態。在公民意涵裡,創造力需要被合法化以成為有效、值得稱道的活動。它獨特的特質集中在城市如何做為整體運作的熱情和願景,而非各自孤立的計畫 ─ 儘管這可能牽涉更大的問題,例如地方為兒童興辦遊樂區的舉動,會被視為質疑市政府不關心年輕人。釋放這種集體能量,可以激勵和賦予民眾及民間組織公共與私有資源,以提供更好的社會成果、更高的社會價值及社會資本。然而好的意圖經常會受到規避風險、內觀文化所阻撓。
「公民創造力」的概念也許看起來不太一致,但這卻賦予它力量:在張力點(tension point)緊握兩個我們很少相互連結的特質,「公民」使人尊敬,而「創造力」令人振奮和進取,它應該成為城市領導的風氣。

相關的抗爭
當城市的光與影逐漸清晰,其氣氛也在變化。許多人覺得他們必須對抗主流的樣板與敘事方式,相信一定有另一種城市形態能夠以不同的原則運作,但是在市場邏輯與資金流決定城市建設的同時,實在難以達成。他們問,最大的資金獲利是否能創造我們要的城市,當知道「不是」時,他們就提供替代方案。
大量的熱錢在全球流動,尋找投資的機會,而房地產開發有其特殊的吸引力。這往往會導向閃閃發光但缺乏個性的高樓,或是使人情緒高漲的購物中心。這些要角有強大的遊說能力,能說服政府讓他們多蓋一層、甚至是十層樓。他們成功地改變土地使用,讓利潤更加豐厚,而他們往往能取得最好的地點,例如河岸第一排,但那應該是讓大眾共同活動的空間。類似案例不勝枚舉。而公共利益與私人倡議計畫相互交織,讓周遭社區有發言權的對比案例,大都能獲得更好的觀感。
可以有另一種城市
土地所有權是驅動力,但土地是相當稀珍的資源。擁有者的信念,決定後續可能發生的事情。它是否能為其城市發聲或予以回饋,它是否鼓勵互動或各自為政。現在有一種趨勢,即尋求政府認同的祕密計畫。理解他們的城市並非由一連串的計畫組成,而是把城市視為一個整體的計畫。
綜觀評論家關注的一個主題,是該如何在出現問題時,把我們現行系統的成本與損失社會化,且把利潤私有化。歷史上最大的案例,是2007、2008 年時西方世界政府,出手拯救了那些操作無法持續金融產品而導致許多人陷入貧困的銀行。以規則為基礎的制度已然消失,這種缺乏監管的狀況持續地引發更頻繁的金融危機。有些人形容這個過程宛如政府被企業綁架,在許多國家更導致「竊盜統治」(kleptocracy)─這是一種偷竊形式,腐敗的領導者利用他們的權利去剝削人民與資源,以擴張個人的財富與政治權力。
反擊已經開始了,但它是否夠強大,抑或僅僅是風中的一小粒塵埃?要創造另類的都市發展形態,我們需要替代性的金融思維,這可以分成五種類別。道德銀行,其首要原則是不把利潤最大化,而是達成一個公共利益的目標:諸如歐洲的三重奏銀行(Triodos)、GLS銀行、環境銀行(Umweltbank)、道德銀行(Ethikbank),以及美國的都市夥伴銀行(Urban Partnership Bank)和春天銀行(Spring Bank)。在亞洲,為窮人而設立的銀行相當艱難,其中,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最為人所知。
第二種形態是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這在澳洲與美國相當流行,它們採會員制,所有的利潤都會回到社區。住宅合作社(Building societies)也同樣由會員組成。它源於英國,但其中許多在柴契爾政府下私有化,每位成員僅分到一點利潤,因而喪失了社區精神。相反的,在丹麥,低價銷售的利潤被保留成立了丹麥地產基金會(Realdania),其資產現在超過了三十億歐元。這些資源被用來改善丹麥的城市環境景觀,以確保後代子孫能夠受惠。還有社區的融資計畫,譬如當地人可能集資來拯救他們喜愛的酒吧、受威脅的書店或成立當地的能源公司。最後,則是網路借貸(peer-to-peer)和群眾外包。
對於傳統銀行的不信任非常強烈。透過比較網站uSwitch.com的一項調查,可以證明我們對替代性金融的嚮往。它發現77%的英國人寧可選擇擁有百貨公司與維特羅斯超市(Waitrose)的約翰.路易斯集團(John Lewis Partnership)做為他們的銀行,它的八萬六千名員工都是該企業的合作夥伴。其成效反映在各商店更積極的服務與氛圍中。
.png)
綜觀城市的領域,有無數的新作法能夠讓事情變得不一樣。它們是思想戰爭的一部分,儘管相互呼應,卻未能被架構成一個偉大的故事。
變遷網絡(Transition Network)是一個讓社區聚集起來重新想像與改造世界的運動。它是在地公民參與和世界網絡的結合。2005 年第一個稱自己為變遷鄉鎮的是英國的托特尼斯(Totnes),這個網絡現已擴散至全球五十個國家的無數鄉、鎮,城市或學校。在最新的一次統計中,已經累計有超過一千五百個計畫在進行。他們的目標是「透過地方性的計畫來應對我們面臨的挑戰。聚在一起,我們就能集思廣益找到解決法案」。他們尋找能夠推廣在地食品的方案,尋求可以降低能源使用的移動方式、鼓勵搖籃到搖籃(cradle-to-cradle)的設計思考與商品製造,並且設立了讓一切都在當地範圍內循環的替代性貨幣。
跨歐洲商場(Trans Europe Halles)是一個由市民和藝術家發起的文化中心類型,自1983 年以來,一直是把歐洲工業建築轉型為藝術、文化與社會運動的最前線。它現在有九十個會員,且試圖「強化非政府組織文化中心的永續發展,並透過連結、支持和推廣來鼓勵新計畫的誕生⋯⋯提供學習和分享的機會,從而促進藝術與文化的實踐、影響與價值」。一些建物如赫爾辛基著名的電纜工廠(Cable Factory),便是該網絡的成員之一。
社會影響力製造所(Impact Hub)網絡在五大洲擁有一百多個中心與超過一萬五千名成員,它為社會創新者提供空間、社群及全球平台。它們是「創新實驗室、商業育成中心和社會企業社群中心的組合,提供你獨特的生態系統,有資源、靈感和協作的機會,以擴大你工作的積極影響」。2001 年成立於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截至2016 年仍是那些想要挑戰社會現況者的全球聚會場所。由於參與人數高達十萬人以上,會議後來移到孟買(Mumbai)、奈洛比(Nairobi)、突尼斯(Tunis),甚至一度在北半球的蒙特婁(Montreal)舉辦。它的標語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印度作家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更喜歡說「另一個世界不只是可能,它已經在路上了」。該組織說自己是
……一個複數、多樣化、非政府與無黨派的開放空間,促進參與的組織與運動(movements)之間,去中心化的辯論、反思、建議、經驗交流和具體行動的結盟,從而建立一個更團結、民主和公平的世界,建構新自由主義的替代品。
它故意在每年的1 月,與其偉大的對手─在達沃斯(Davos)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同時召開會議,以便向世界經濟問題提出替代性的解決方案。
這些計畫、組織和網絡非常重要。它們為我們的世界帶來活力、能量和解決方案,這些在經過奮戰與時間的考驗後,通常能被主流所接納,儘管可能慢了好幾拍。
它們就像散落在世界裡的積極碎片,但是否能聚集在一個城市呢?在我擔任柏林博世學院(Bosch Academy)院士期間,思忖柏林是否能成為這樣的示範。我並非認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哥本哈根因為其永續性的發展也是一個很好的典範,而波隆那在利用其公民想像力部分也有極深厚的傳統。麥德林從一個謀殺之都到現在努力改善其貧民窟現象的劇烈變化,也讓人深受啟發。巴西的庫里奇巴(Curitiba)依然是一盞明燈,前市長海梅.勒納(Jaime Lerner)的都市針灸術非常有效,讓這裡成為一個綠色之都。他在1972 年的第一個計畫,是不顧強烈阻力,把主要車道改為步行區,而且是在四十八小時內迅速完成。從此,該市就成為城市規畫的創新典範。當然,還有許多案例不及備載。

事實上,許多人認為柏林在某些方面並不一定有創造性。然而,從其歷史來看,許多人為了避免兵役搬到西柏林,促成了反抗的傳統和無政府主義的氛圍。當這個城市再度一統後,擅自占地者大量湧入邊境建築,許多後來被就地合法,其居民成功地突破可能的界線。柏林現在最知名的當數由電音主導的俱樂部文化,但其實還有更多。它公民運動的傳統促使當地政府專注於自行車文化及永續生活的各種形態。它東西方統一的狀況,意謂著有許多住房及堅固的工業建設,握在市政府的手上,而且這裡還有合作住房的傳統。隨著柏林受歡迎的程度,士紳化也快速地進行著,威脅城市的平衡。激進人士也進入政治體系,尋求能夠制衡這些過程的辦法,有時甚至以買下產權的方式,來保護它們避免受到炒作。其中對於管理、誘因及如何展延既有的法規,有激烈的討論,例如擴充土地使用分區法,好讓社區裡能有更多元的商店組合。另一種方法是,只把市政府土地賣給那些被審定為最好的計畫,而不是給提出最高買價的投資者。有一個特殊的趨勢是,基金會和社區及社運人士合作,買下重要的地產,把它們帶出市場。總部在巴塞爾(Basel)的瑪麗安基金會(Maryon Foundation),在德國新克爾恩(Neukölln)最時髦的市中心保存了大半的金德啤酒廠(Kindl Brewery),做為非商業、主要為文化使用。它過去也是非法占用的空間。另一個案例則是由迪亞斯基金會(Trias Foundation)認養的Rotaprint 印刷廠區。同樣來自巴塞爾的阿本德羅特基金會(Abendrot Foundation),其收入來自保險業,後來發展出反核運動,並資助了有指標意義的Holzmarkt 合作社土地開發案,這在全球資產投資來說,是一項極度不尋常的實驗。該土地前面的兩百公尺長河岸,有柏林知名的夜店Bar 25,它非法占用土地,因此展開了一場象徵性的戰役。一旦Bar 25 被迫撤離,市政府想建設一個高樓區,然後把土地出售。抗爭者以「斯普雷河是大家的」(Spree für Alle)為口號,阻止該區域變成傳媒特區。Bar 25 的支持者找到阿本德羅特基金會,打敗其他避險基金,以一千萬歐元買下該片土地,然後再把它回租給Bar 25 常客所創辦的合作社。這個合約非常特殊,因為不論是合作社或基金會,都無權把該地產出售牟取利潤。
Holzmarkt 開發計畫的整體價值已經超過一億歐元,它是一個複合式的環境,還有火車以高架橋從高空經過。Holzmarkt 的彈性讓它能夠和鐵路公司交涉,提供一些土地讓它存放物資,以換取這些有趣設施的使用。它的長期財務,將由河岸一端的酒店營運及另一端「Eckwerk」(工作角落)的複合式建築開發來支持。這是一個由五棟十層樓高木構建築所組成的聚落,是德國最高的木造房屋。其空間將出租給學生及一個以創造活力社區為目標的育成中心。Holzmarkt 形容自己是一個村落與一群亂七八糟的組合,基本上不可能出現在這樣的黃金地段。它的中心是一所幼兒園與一個製作工坊,它也經營市場,有活動場地,還有一間餐廳和烘焙坊。第一階段飲食的收入將用來償付貸款。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可以親近河岸,而在河的對岸則是柏林最大的合作住宅區之一。在開發過程中,四個區段共聚集了二十五家公司,收益較高的活動可用來支持較不賺錢的。
其他計畫的資金則來自於一系列有同理心的另類銀行,以及一個由一百五十人組成的互助會,每人都投資了兩萬五千歐元的股份。包括最高金額借貸方的每個人都只有一票,整個計畫則是由一個合作架構來管理。因為極具象徵意義,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遊客到此參訪,尤其是市長們。Holzmarkt 現在已形成一個都市發展替代計畫的網絡,成員包括特拉維夫的維恩(Vemm)、阿姆斯特丹的聚集計畫(Gather)及基爾(Kiel)的老穆(Alte Mu)。目的是要把這個理念拓展至全世界。一個潛伏的危機是,Holzmarkt 如果變得太受歡迎,就可能觸發它原來想要避免區域士紳化的結果。我們將持續觀察,它是否有助於系統性的改變,希望依然存在。
書籍資訊:
《遊牧世界的市民城市:探討未來新生活型態城市創生發展新思維》
作者:查爾斯・蘭德利 Charles Landry
出版社: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日期: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