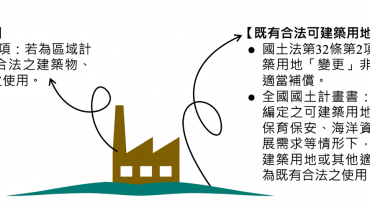文:黃子芸(環境法律人協會研究員)
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的土地使用管制間所存在的差異,導致在制度轉換的過程中,原本合法可建築用地將可能被劃設入「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並產生現在使用與未來管制的可能衝突。因此,土地使用管制的限制與既有權利的保障,儼然成為在土地使用管制制度中的重要討論議題。討論這個議題的起點,便是釐清國土計畫中,適宜性分區的概念。
國土計畫如何創造空間秩序?就是劃設適宜性分區
國土計畫是將土地依自然環境特性,以及空間佈局中被賦予的角色(如:因應發展需求、城鄉發展願景)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功能分區。並且,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以「計畫引導使用」模式實施管制,來促成國土規劃成果轉化為得以實現的空間秩序。
因此,於國土法第21條中,即規範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的土地使用原則,像是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為維護自然環境狀態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應儘量維護自然環境狀態,僅允許有條件使用。或是,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以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為主,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並依其產業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但讓我們想想一個情境⋯⋯有一間合法工廠已在一地營運多年,但在功能分區公告後卻發現位於農業發展地區中,這時應該如何實施管制呢?直接以不符國土功能分區的土地使用原則為由,要求工廠遷移,以避免其成為計畫管理下的凍結區域,導致國土管理的破碎嗎?
再進一步地說,這塊土地上曾有的工廠早已拆遷,那在國土計畫體制上路後,應該繼續保障這塊土地的建築權利嗎?
換言之,因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的土地使用管制間所存在的差異,導致在制度轉換的過程中,原合法可建築用地將可能被劃設入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並產生現在使用與未來管制的可能衝突。因此,土地使用管制的限制與既有權利的保障,儼然成為在土地使用管制制度中的重要討論議題。
國土計畫體制中對於既有權利保護的承諾
原有的建築物與土管不符時,可以繼續使用,但只能修理不能新建
國土計畫法第32條第1項中針對建築物與設施物提到「區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與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不符者,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建。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斟酌地方情形限期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其因遷移所受之損害,應予適當之補償」。
原有合法的建築用地,未來儘量規劃成可建地,否則應適當補償
國土計畫法第32條第2項,則針對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進一步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償」。於立法理由中並陳述,基於計畫理想、土地使用計畫體系穩定、民眾意願及財務可行等考量下,未來於擬定或變更國土計畫時,將透過規劃方式儘量維持為建築用地。惟經評估確實仍有國土保育保安需求,而應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者,依據司法院釋字第525號解釋,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償。
又於全國國土計畫書中,述明「保障既有合法權利,允許土地使用」為土地使用基本方針,因此,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在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海洋資源維護、農業發展需求等情形下,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或其他適當使用地,並得為既有合法之使用。
簡單地說,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並不會豬羊變色,既有的建築物可以繼續使用,原本合法的建築用地,國土計畫會保障原有的使用權利。
土地使用管制限制與既有權利保障的取捨之間
在已承諾保障既有合法權利、得為既有合法使用的情境下,土地使用管制限制與既有權利保障的討論等同將聚焦於二者衝突範圍的界定,並拘役提出解方。若從法制觀點切入,對於衝突範圍的界定可以透過兩個問題來分析:
信賴保護:保護人民對於政府行政正當合理的信賴
衝突的界面是「信賴保護」的範圍,關鍵的問題是:「受土地使用限制的土地所有權人可否主張有信賴保護?」其中,「信賴保護」是在符合「信賴保護要件」(有信賴基礎、有信賴表現、信賴值得保護)下,給予「損失補償」、「存續保障」及其他合理補救措施。
特別犧牲:公眾利益致財產利用受限,形成其個人利益之特別犧牲,自應享有相當補償之權利
衝突的介面是「特別犧牲」的範圍,關鍵的問題變成是「所受土地使用限制是否屬於社會責任或社會義務範圍?」「特別犧牲」與「社會責任/社會義務」的認定界線則又相對模糊,並再涉及「是否妨害財產權本來效用發揮 / 侵害財產權本質」、「財產權限制是否是為了調和社會共同生活」、「限制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正面效果或防止負面外部性」等。
整體而言,恐唯有針對每筆土地狀況進行判斷,並對個別情境更細緻地從限制的目的、手段及結果進行衡量判斷,對應不同的土地類型、不同目的及限制強度等解釋,才得以藉此摸索既有權利的保障與計畫管制的效力平衡點。
國土既有權利保障的再議空間
因此,從土地使用情境的複雜/多元性來看,不免要質疑的是:國土計畫體制中對於既有權利保護的手段是否推論過快?是否忽視對「所受土地使用限制是否屬於社會責任或社會義務範圍」的討論?
特別是,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是以功能分區分類作為土地分類的方式,並據以界定合適的使用方式並進行管理,其中或已隱含了土地使用須回應外部性義務、避免外部性傷及周邊使用的權利,亦與前述法制觀點中,對「所受土地使用限制是否屬於社會責任或社會義務範圍?」的思考已不謀而合。換言之,若以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作為既有權利保障的出口,則「土地使用限制的財產權社會責任與特別犧牲界線」,顯然是個亟待取得公眾共識的重要命題。
若回到國土計畫觀點,以「建立一套能有效引導土地使用行為的土地使用管制系統」的核心目標而言,更需要討論的或許是:「欲建立的土地使用管制系統」即等同於「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的擬定」嗎?
當制度設計上採用「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作為既有權利保障的唯一解方之際,或已忽視規劃手段的多元性,排除計畫引導的可能,並將國土管理暴露於風險當中。土地使用管制並非空間規劃的全部,在既有權利的保障中,除了同等就地合法的保障機制外,更應思考的是計畫引導的手段設計。藉由民眾參與及討論,共同尋求衝突的解決途徑,以將既有使用藉由制度化的機制把關、引導及協助,逐漸收攏。
如此才是我們期待、具有公平機制的土地使用管制系統,而非放任不適宜使用及其外部性成為國土發展的威脅;也唯有如此才能真的有效的促使「對的事情,發生在對的地方」!
黃子芸,誤入環境法律NGO的都計人,環境法律人協會空間政策研究專員。
環境法律人協會(Environmental Jurists Association, 簡稱EJA)是由一群關心環境的法律人所成立的環境法律NGO/NPO,期待透過環境議題的參與及研討,發掘環境法制的缺漏,為台灣的環境永續奠定穩固的基礎,以確保符合世代公平正義的自然生態、經濟及人文環境之永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