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巧惠
插畫:Hui
在城市出現以前,我們先有了街區。在裡面吃飯、走路、做夢,像是一席席流動的饗宴。
不同的街區在各種時空條件的影響下成形、變異或消解,深耕於城鄉發展領域的觀察者、研究者與行動者,在此間挖掘街區的價值,參與地方的擾動,看見人的活動。當他們談論各自與街區的交往,也描繪出街區理想的形狀。
對談人簡介
侯志仁 ∕ 美國華盛頓大學地景建築系教授,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環境規劃博士。主要專業領域涵蓋社區設計、城市共生與公共空間,著有《城市造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反造城市:台灣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反造再起:城市共生ING》。
連振佑 ∕ 中原大學地景建築學系副教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提倡社群協力營造社區,努力促成Place-making、地方再生,以Temporary Urbanism理念促進空間分享;致力以參與式規劃設計手法,邀請關係人共同邁向協議、自治及共享的生活環境。
施佩吟 ∕ 原典創思規劃顧問有限公司副執行長,畢業於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9年起陸續透過不同的實驗行動,發展多樣態社群網絡計畫,包括羅斯福路沿線綠點營造、Open Green打開綠生活、社區交往等計畫串聯。
Q:各自曾以何種方式,陪伴或參與街區再造的現場?
施:「小柴屋」的案例雖然微小,但給我的衝擊還滿大的。
一開始是我們發現台北竟然還有木材街、打鐵街,這裡的師傅是設計產業加工、打樣很重要的支持機制。除了促成外人看見這個產業街區,我們也想讓街區裡不同的社群、在地人或店家,有機會看見彼此。
後來在保安路上發現一間長期荒廢的破屋,這裡竟然還有這種屋子、庭院、人行道、街道層次分明的空間,人來人往很容易去打招呼、去認識,我們就借重街區師傅的技術改造成小柴屋,邀請各種社群和行動進駐。「柴寮仔」的故事在過程中慢慢被當地人談起,小柴屋成為街區裡可以自然聚集又發散的一個節點。
連:我想到比較早期的桃園新民老街改造,街區在時間的催化下可以產生很多變化。
這條街上有老屋、有美食店、有很多生猛的元素,要一體適用地想像如何改造,其實很不容易。我覺得街區再造就是要有時間和耐性,還要向當地學習。我們設了一個駐地工作室蒐集改造意見和街區情報,慢慢摸熟這條街。
因為政府標案的限制,最後主要是做鋪面、雨遮、水溝蓋的改造,2008年完工後我曾聽過批評的意見,我覺得這也很好,表示有人在關注這個地方。現在有年輕人在做桃園舊城導覽,街邊上也開了咖啡廳,我們所做的或許點了一把火,引發更多年輕人在這裡活動,讓老街不斷往前。
侯:我講個更久遠的案例,在台灣第一波社造中,我負責宜蘭五結的利澤簡。這條老街因為有冬山河的運輸優勢,早年相當繁榮。但當時的實際空間已經看不出來,大部份居民也都在外地工作,很難做所謂的街區再造。我們想了很多方法,後來把重心放在地方慶典的再造。
這裡每年元宵節都會舉辦「走尪」(台語tsáu-ang),雖然是一個很有歷史的慶典,但因為是宮廟活動,居民大多只有看熱鬧的份。我們結合學校參與,也有夫妻協力競走的另類走尪活動,讓老街原有的傳統宗教慶典,變成一個更多人同樂的創意活動。
這個案例並不是硬體或產業的改造,它是一種認同的改造,讓街區和生活可以更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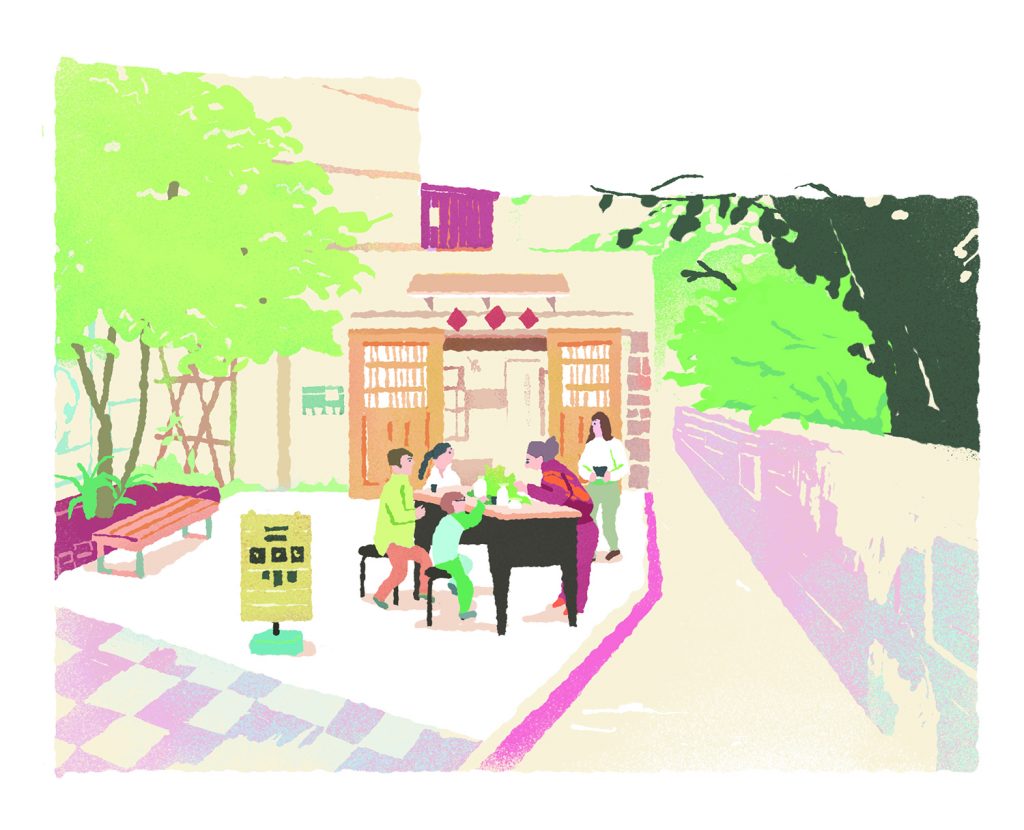
Q:請分享國內外,精彩的街區想像和行動?
施:通常我們參與擾動之後,會希望街區長出自發性的行動,加蚋仔就有這樣的演進。
前期我們找來在地音樂文化工作者──勞動服務,用節慶式的廟埕演唱會、唸歌遶境,連結年輕人對家鄉的認同。後來台大城鄉所一群學弟妹成立「好加在工作室」,重新梳理加蚋仔的價值。在這些專業性的介入之後,有一批年輕人組成「六庄文化發展協會」,為當地學校做街區導覽,最近也設計實境遊戲,重現這條老街支持的百年聚落生活。
連:嘉義溪口老街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這幾年許芳瑜老師在這裡駐地輔導,逐戶拜訪、盤點裡面的網絡關係,2020年開始「溪計畫」的行動。他們把採訪故事結合當代美學手法,例如在老相館前用攝影棚的意象做為時空體驗的入口;將街區原本很生活性的部分,例如打陀螺、尪仔鏢等傳統遊戲,變成展演性質的呈現。我要強調活動不是只有表面的熱鬧,前期有很多綿密的準備工作。
就像侯老師的「走尪」,軟體才是活化整個空間的核心。溪計畫和新民老街原本都來自景觀空間改造的專業者及其起心動念,最後我們發現真正的議題從來就不是空間,真正會活起來的是街區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侯:那我講自己在國外的案例。西雅圖國際區是一個亞裔的歷史街區,有很多老建築和不同族群的居民。因為1970年代美國城市開始郊區化,20年前我們進場的時候,這裡已經是一個頹敗的社區,族群間爭執不斷,資源也不足以支撐大型改造。所以一開始,我們選擇介入尺度比較小的空間,推動過程相對容易,像街道綠化、小型公園改造,後來才有大一點的社區公園擴建之類的案子。
過程中我們和當地團體合作,也協助成立新的組織IDEA Space,透過這些組織爭取更多經費和資源,讓街區事務可以常態性推動。幾年下來街區有非常大的轉變,有更多元的店家進駐,有在地開發商投資住宅改建,當地團體也開始有自己的行動,把一股新的活力帶進來。
施:我們目前所思考的街區,還是以平面性、街道性為主的2D概念,但未來可能有越來越多的垂直和立體化。東京SHIBAURA HOUSE把街道元素融入垂直性的空間,創辦人伊東勝認為街道上就是要有像公園一樣的開放空間,像家一樣溫暖的活動,像社區一樣具有認同感。這樣的未來性街區,將是一種認同的匯聚。
Q:認為理想的街區環境,應具備哪些元素?
侯:就剛剛的幾個案例來盤點,一個理想的街區會有它的紋理、尺度,和既有的人際關係。最好能有街區組織,像佩佩說的六庄;有專業者的參與,例如連老師講的嘉義溪口的案例。這些都是成就一個理想街區環境的主要元素。
連:人情味是我第一個會想到的,在多重的社會網絡裡面,有非常多樣的行動者,這些行動者用比較傳統街區的說法,會有雞婆、阿信之類的角色。裡面會有很多熱情的節點,交織出複雜的關係。街區的複雜性是必要的,因為單一就會無趣,只能競爭類似的消費者。
街區會從硬體、行動和人物的種種細節,發展成許多故事,豐富將來被寫下的歷史。最後,裡面必須有交換,而且是各式各樣的交換,這也和前面的元素互相解釋,行動者之間有策略或目標的交流,節點之間有資訊的交換。
施:如果要具象談理想的街區,我覺得就像逛夜市發現這裡多一攤雞蛋糕、那一攤豬血糕沒加香菜,街區的流動性和變化性是不斷發生中的,而且往往會帶來意料之外的驚喜。
街道不只是一個線性的空間型態,它所指涉的產業、歷史或社群等等的活動,發展出多樣的生活,這個多樣性來自於許多使用是暫時的。還有侯老師說的開放性,理想的街區就像剛剛舉例的夜市,允許任意加入或離開,允許試誤的實驗行為,允許出其不意的使用,形成錯落的活動和空間運用。
侯:開放性是一件值得討論的事。我們通常會希望街區是穩定的狀態,例如它的人際關係或認同,可是城市一直都在變。例如疫情當下,需要更多的人際互助,需要更多的開放空間,讓居民透透氣。我們如何看待一個街區的轉變,街區如何去回應這些新議題,我想這是一個滿有趣的課題。

Q:最後,請分享各自生命經驗中「自己的街區」。
施:我從小在新店惠國公有市場長大,對街區的最初印象就是那樣的環境。那裡類似一個城中城,一樓是傳統市場,二樓是住家,我天天都會穿過市場回家或串門子。我媽當年懷著我北上到舅舅的水果攤工作,很多原鄉親戚也在這做生意,這樣的經歷養成我容易和人自然熟的性格。
當代社會常講公共空間佔用或公安問題,但對當時的我來說,生財器具堆出攤位外,小孩在通道邊擺桌子寫功課,都是平常的生活樣貌。惠國市場現在被新北市都更處認定是危險建物,只剩下周邊和巷子裡有攤販。
連:其實我家不在大甲街仔,在我小時候要經過一條有樹有河蜿蜒的巷子,我會上街看中藥房師傅踩藥船,到雜糧行把豆子弄亂,沿著店鋪的騎樓漫步。後來大甲街周邊的巷子一條一條不見,都市計畫的道路一條一條打開,拆掉我小時候會經過的老房子,我常爬的樹、抓魚的小河都沒有了……
我覺得我的身體感消失了,不是找不到熟悉的店家,而是那些新的、棋盤狀的街道,摧毀了我的身體移動經驗。或許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懷舊或鄉愁,但我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是身體經驗的不見,那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侯:我的故事跟連老師有點類似。我小時候住在台北的八條通,以前的條通和現在完全不一樣,是一個單純的住宅區,我在那邊出生,一直住到國小五、小六年級,大部份童年都在這條巷子裡,條通就是我的全世界。那時候巷子裡有好幾個同齡的小朋友,只要在巷口喊一聲,所有的朋友都會下來玩,這裡就是我們的遊戲巷。 大約是1970年代中期,隨著台北的發展,路上車子越來越多,條通也變得不太一樣。有一天我的朋友在巷子裡被車撞傷,後來我們就幾乎不在這裡玩了……不久後我家搬到東區,東區巷弄不像條通那麼好玩,回想起來滿像電影的剪接換場,街道的轉變,連接著我童年的結束,以及一個世代的落幕。
延伸閱讀:何謂街區?侯志仁、連振佑和施佩吟的對談筆記(上)–街區的生成與形狀
《地味手帖》是台灣第一本關注新生活型態的MOOK,面向包含移住、創生、職業、居住、街區文化等種種不同生活價值觀,每期探討一個特輯主題,試圖將隱性的現象化為明確的趨勢。內容中,更邀集多個深具地方文化和現況的作者專欄,打造成一本「生活有著開闊可能」的風格指南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