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王惇蕙|編一點點:Christine Lee
編輯引言:作為二月《做孩子事、和孩子一起做事的亞洲城市》客座主編的我,是在三年多前,認識時任國立臺灣美術館助理研究員推動臺灣兒童藝術基地的惇蕙;從那時候起變成同溫同路夥伴之外,開始一起從遊戲空間往文化場館空間位移,從內、外部協力,倡議藝文博物空間和休閒娛樂活動的兒少遊戲權及兒少參與表意權。
讀這一篇邀稿前,先有個初淺提問,是:為何亞洲普遍對 12 歲以上青少的休閒娛樂重視程度,不如對學齡前或學齡;重視課業成就的社會,對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的 0-18 歲兒少,對其「享有休閒、從事適齡的娛樂活動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的權利」重視程度,是隨年齡增加而大幅下降。而當孩子長成可以說話書寫的生物後(大約 9-10 歲開始?),成人就開始高度期待孩子玩的模樣、表意參與的形式,可以就直接變成「像大人那樣」或用「大人的方式」,忘記了他們從兒童過渡到青少的(因多元個體而異)幾年過程,是需要來來回回被給予大量的自主選擇、彈性空間、信任和愛 — 許多亞洲社會習慣用大人想像中的青少,去規劃政策、空間、設施和活動,加上善用兒少代表、兒童青少委員、學會幹部、青少大使、實習志工等名義 — 有的認定他們是兒童、有的認定他們是大人,但從兒童青少變成大人過程並非線性一致,青少經常有既是兒童也是大人的疊加態、既非兒童也非大人的獨特。
因此,當我看惇蕙這一篇(或她此刻在傅爾布萊特計畫獎助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工作過程中寫回給台灣的每一篇),都是亞洲社會中每個博館工作者或友善城市倡議工作者作為參考的方向。回到一開始的初淺提問,兒少領域工作者如我們,需更理解服務關注的對象,並用更多的多元方式去互動、授權、共作和支持。
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The Children’s Museum of Indianapolis)以青少為對象的計畫,可追溯至 1960 年。創立之初,名為「青少詮釋/導覽計畫」(Junior Docent Program),以較為穩定且可控制的兒童博物館為場域,讓社區的青少在此體驗兒童博物館的各種工作(主要體驗展場服務工作);1997 年,轉型為「青少夥伴計畫」(Youth Partnership Program),該計畫不只包含了兒童博物館的青少夥伴,也有印第安納波利斯在地多個且不同類型的青少團體參與。此次的轉型,可以明顯看見青少議題逐漸為人所重,然僅限於範疇擴張,仍以社區服務為主。
專注於青少的「自主性」:博物館(青少)學徒計畫(Museum Apprentice Program/MAP)
2004年,計畫正式更名為「博物館(青少)學徒計畫」,因應時代變遷更新計畫目標:以自主性為核心,培養深思熟慮的思辨者、積極行動的公民(博物館定義自主性包含了技術/能力、同理心、責任感、社區/社群意識 4 大面向)。
撰文此刻,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總共有 31 位青少學徒。由於被選進青少學徒計畫者,可以在團隊裡待到年齡上限(18歲)再離開, 因此今年僅有 12 位是新加入的成員。想加入計畫的青少,必須於上半年關注網站最新消息,並在每年 4 月釋出名額時提出申請;所填答的內容,由館方負責計畫的 3 位成員(Lauryn, Julianne 和Morgan)緻密討論與初步審核之後,選出具有潛力的青少,進入第 2 階段進行面談與團體面試(多半在夏季舉辦)。
博物館(青少)領袖計畫(MAP Leaders)
面試青少學徒的人員,除了 3 位館員,還有「博物館(青少)領袖計畫」的成員。「博物館(青少)領袖計畫」將博物館視為青少領袖參與與發聲的場域,青少領袖藉由實際帶領「博物館(青少)學徒計畫」增加專案管理的實務經驗,進而增加自我覺察能力與建立自信。
每一位青少領袖都經歷過學徒計畫,此舉不僅是經驗的傳承,更重要的是青少領袖能在對兒童博物館有相當認知的前提下,提供館方有關「青少+博物館」的建議。值得一提的是,青少領袖被定位為青少學徒和兒童博物館之間的橋樑,他們和館方決策團隊有相當密切的接觸,能實質影響館內的青少相關計畫,同時也能穿梭於館方與青少學徒之間,傳遞雙方各自在意且認為重要的大小事。
青少學徒、青少領袖的創意成果
雀屏中選的青少學徒、青少領袖在博物館密切合作 9 個月,期間每個月都會和館員開會討論 2 次。館方不會強制規定他們要在 9 個月做什麼、怎麼做,而是鼓勵他們自行開發專案,提供實質上的協助(負責專案的同仁說,博物館只規定了兩件事:一、至少七成的會議出席率;二、每學期至少參與 1 場家庭觀眾專案活動或公關行銷活動)。
青少領袖和青少學徒過往開發的專案五花八門,像是 2021 年製作了 17 集的podcast 節目,青少們透過研究、書寫、錄製 podcast 的方式,向大眾說明數年前聯合國提出永續發展目標及其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當下的人們能做些什麼補償措施。

(https://sites.google.com/view/map-news/home)
在 2022 年至 2023 年,青少們製作了專屬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的繪本,每一位成員都被分配到一個角色(編輯、作者、插畫家等),藉由「合作產出繪本」的過程,探索說故事的不同角度與方法。令人驚喜的是,這一系列的繪本也回應了博物館強調的「共融」,像是館內提供了哪些感官友善的服務等。

今年適逢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創館一百週年,青少們當然不能缺席。撰稿期間,筆者有幸參與了幾場青少們規劃辦理的活動,像是兒童博物館每年跨年盛事:中午的倒數計時,青少們討論、設計、產出了一本給家庭觀眾的創意體驗資源,其專業程度讓人驚艷不已;接下來的幾個月,他們也將持續以博物館的 100 歲生日發展系列活動,讓大家知道青少在博物館能做的比想像的更多、能發揮更多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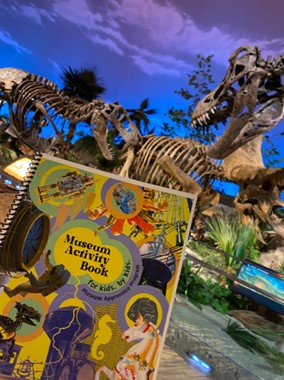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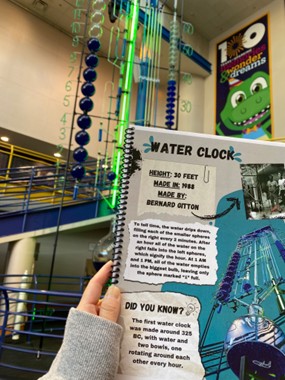
兒童博物館作為青少的支持者
青少學徒和青少領袖在計畫期間,會受到來自館方的各種邀請:在展覽規劃階段,他們曾被邀請作為觀眾研究的焦點團體,提供最切身的建議;也曾在典藏物件的選擇上,給予最貼近青少的觀點與見解。對兒童博物館來說、是最了解青少與趨勢的的諮詢對象、是彼此交流讓靈感大迸發的重要夥伴。
看似龐大的 2 個計畫,館內僅有 2 位正職員工(Julianne 和 Morgan)、1 位兼職員工(Lauryn)負責。其中,除了兼職員工 Lauryn 具有教育背景,其餘兩位學術養成分別是生物學(Julianne)與考古學(Morgan)。好奇的筆者詢問兩人對青少業務的熱忱從何而來?兩位皆提到以往工作與青少、社區、公關行銷活動的經驗,並持續地和青少一起工作、互相學習來充實自己。
文末,筆者想分享 Julianne 與 Morgan 提出和青少共事的建議:
相信青少、樂於分享,找到彼此的共識並傳承下去
聆聽青少、保持彈性,一起腦力激盪找到好玩的事
根據筆者過去在臺灣博物館與美術館工作的經驗,在館所裡很少看到青少的身影,更遑論青少在博物館主導些什麼、做些什麽有趣的事情。然而,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是「兒童」博物館,青少大多討厭被貼上兒童的標籤),筆者看到迥然不同的情境:從發想到執行,青少們主導著大小事,只有在需要幫忙的時候,會回過頭找堅強的後盾(Lauryn, Julianne 和 Morgan),她們三人會想盡辦法幫青少創造連結(誰在館內能幫忙?哪裡有資源可以用?)接下來就放手讓青少們自己去探索。
筆者認為,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青少學徒計畫如此有意義,來自於大人對於青少根本的想法:在這裡,青少被視為擁有主導性、能被信任的主體,他們知道自己要什麼、知道館內的大人可以被信任(有時候也能被挑戰)、知道自己想要的事情是可以實現的,會更願意投注心力參與過程。
筆者也以為,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青少學徒計畫走過逾 60 年,仍有相當影響力,和大人回應青少的方式脫離不了關係:他們總是保持距離,跟在青少後方。當青少迷失或擔憂時,可以並肩前行走一小段。但是,他們絕對不是那種走在青少前面,逼著青少走向同一個未來的大人。
後記:本文感謝 The Children’s Museum of Indianapolis(特別是 Julianne 和 Morgan)大方分享經驗,以及傅爾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大力支持。
目前蹲在全世界最好最大的兒童博物館(印第安納波利斯兒童博物館),看看最多小孩的地方究竟有什麼魔法!
遊走於博物館與美術館、體制內與體制外,熱愛和小朋友蹲在一起學東學西、笑東笑西,被小朋友們加冕為惇惇隊長,成群結隊的目標是要消滅各種無聊、讓世界變得好玩。期待自己一直保有小朋友直率的個性,對平凡與不平凡都能坦率又熱情!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