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采和(本書作者)
本文為鄭采和建築師旅居荷蘭10年之求學、就業、生活之觀察筆記《我在荷蘭當都更說客:阿姆斯特丹以人為本的10年街區再生筆記》之書摘。以下為《我在荷蘭當都更說客》一書第三部分『社會性重建』的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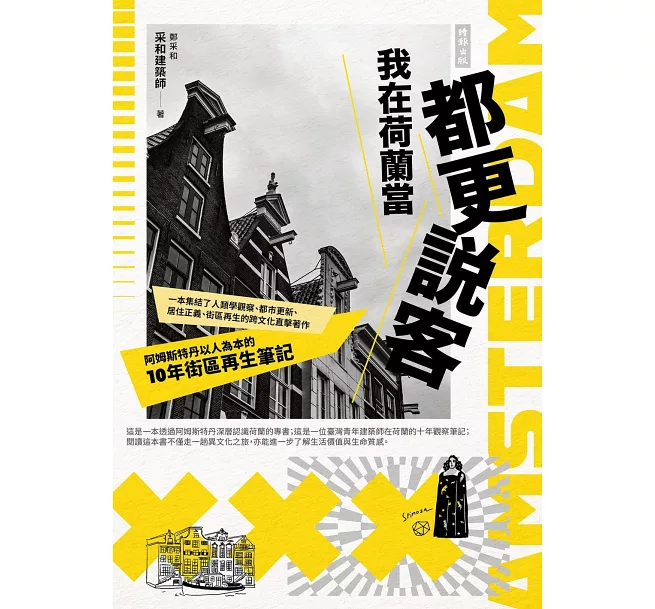
《我在荷蘭當都更說客》新書封面
在漫長的商業殖民史的過程中,荷蘭人與印尼人曾不斷地通婚,後來在印尼脫離荷蘭統治後,有一群荷印混血的族群來到荷蘭,屬於荷蘭新移民之中融合得比較好的族群。可能當時的荷蘭社會也必須接受這些人的關係,屬於兩邊都別無選擇的狀況下而必須採取的融合。他們的混血子女,就成為現在荷蘭人口中的「印迪許」(荷:Indisch/英:Indo People)。
荷蘭第二波大規模新移民的移入,則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荷蘭引進土耳其、摩洛哥及蘇利南的勞工,從事各種勞動工作,諸如造橋修路、碼頭搬運等,一直到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才停止。本來荷蘭人打算在這群勞工停止工作後,就把他們送回土耳其及摩洛哥,沒想到他們陸續申請將他們的妻子及小孩從母國接到荷蘭,當中很多人不願意回去,就這樣,來自土耳其及摩洛哥的新移民,從此在荷蘭住了下來。可能是因為荷蘭人並沒有準備好要接納這批新移民,也可能因為新移民的家長多數是勞工階層而須長時間工作,並沒有時間陪伴他們的下一代,另外還有信仰差異的原因,造成第二代移民與本地社會的撕裂,目前仍是荷蘭現代社會裡一個無解的問題。
自一九七○年代起,民主、自由及公民社會的風潮吹到了阿姆斯特丹,政府鼓勵每個新移民社區擁有自己的宗教型社區中心、學校以及電臺,當時的城市治理政策為「為鄰里建設」(英:Building for the Neighbourhood)。荷蘭社會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對於他們複雜且多種族的社會組成採用支柱系統(英:Pillar System),意即每一個族群、宗教團體都可以擁有自己的活動跟言論空間,有自己的報紙、電視臺、學校、宗教空間等。支柱系統分門別類有天主教支柱、新教支柱、自由主義支柱及社會主義支柱等,每個人都必須進行登記,住在哪裡一目了然。不過這樣聚焦於整合社區既有居民的模式,對於普遍為低收入戶的摩洛哥人聚集街區,並沒有造成太多正面的迴響。
到了一九八○年代,政治人物皮姆.佛杜恩開始公開反對這樣的社會福利及社會住宅政策。他曾經在接受荷蘭人民日報(Volkskrant)的專訪時說:「我討厭伊斯蘭教,我認為那是一個沒有在進步反而是退步的宗教。我常在世界各地旅遊,但是每當我到了有伊斯蘭教的地方,都是可怕、虛偽的地方。他們的宗教準則連聖人都很難做到。世界上除了荷蘭還有哪些地方可以讓同性戀的人當上地方領袖?我希望能保有我們國家在這方面的自由跟意識形態。」直到佛杜恩被謀殺後,才開始有政治人物敢跟著公開反對一九七○年代的「為鄰里建設」—這種讓新移民伊斯蘭教徒可以蓋自己的宗教中心,並拒絕與荷蘭主流社會進行融合的城市治理政策。而當時的政治傾向也開始不談所謂的「文化多樣性」,甚至會有人嘲笑說,這是一種不敢公開承認與新移民存在衝突的「政治正確說法」。於是有些政治人物用「世界公民」為號召,開始宣傳新的城市治理思維。
荷蘭政府面對自己國內的多重文化,及其所造成的各種衝突及融合問題,卻有點後知後覺,背後的因素可能是因為這些外來新移民,往往主要來自他們本國的殖民地,而非像美國,是一個本身由新移民創立的國家。
在阿姆斯特丹,都市重建不只是硬體的城市建設及住宅更新,同時也是人口、種族、社區組成等軟體的再思考。雖然在一九七○年代的多種族專屬社區思維,的確讓每個不同移民文化社區彼此之間的內部居民連結強化了,但卻讓這些社區與整體城市斷了聯繫。也有社會學者研究,在這些各種族專屬社區內,如果新移民是暫時承租戶而住在這個社區,或是長遠的被配給戶或是銷售戶而住在這個社區,其在社區的經濟及文化能量也會不同。他們發現所謂「社會融合」這樣的口號其實不夠具體。他們也發現新移民聚集的社區不一定不好,然而普遍低收入的新移民社區一定不好,然而這樣的低收入社區就算是在白人群體裡也一樣。如果將低收入戶與高收入戶混在同個社區會造成反效果,那麼將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及部分中產階級混在同一個社區就應該還可以。
學者研究如何讓一個新移民社區維持在一定的經濟及文化動能上,這跟這個社區的人口流動率很有關係。譬如華人熟悉的中國城,雖然很多窮人,但是都是希望向上流動的窮人、中國人及藝術家,他們都是暫時的住宅承租戶。嚴格說起來,中國城不是一個貧民窟的概念,它比較是一個經濟的有機體,真正的貧民窟人口是不太流動的。另外,如何維持社區有著一定的向心力是重要的,所以也要有一定同等社會經濟地位的居民團體比例。所以,如何混居銷售戶及承租戶在同一個社區也是很重要的。
近年來很成功的新移民住宅案例,是鹿特丹市的拉.米迪(Le Medi)摩洛哥小區;是一個由一位摩洛哥創業家哈薩尼.伊德里西(Hassani Idrissi)集資興建而成,具有中東風格的住宅兼文化村。拉.米迪小區有九十三個住宅公寓,其小區中間還有一個神聖的大型中庭廣場。圍繞著中庭廣場的廊道,鑲崁著象徵伊斯蘭文化藍綠顏色的馬賽克磚。拉.米迪小區在規劃和興建過程中,不斷受到社會輿論的質疑和反對,批評者認為這種小區只會演變為日後的貧民區。哈薩尼也以為建成後的買家市場只有來自摩洛哥的新移民,卻沒想到建成後,入住戶中有三成是荷蘭白人家庭。這些荷蘭白人都表示:一直很嚮往住在這種帶有異國情調的住宅小區裡!
這個富有強烈地中海風格的住宅小區於二○○八年落成,坐落於鹿特丹西邊的博斯波爾德(Bospolder)區域。它的配置形成了獨立的街廓內街道,晚上還可以獨立將小區關起來。建築師花了蠻多力氣在處理建築物的立面,窗框和門框都被放大並更加強裝飾,建築物的立面採取不同的中東色彩,扶手欄杆及門都有一些額外的細部。在小區的中央有一個方型的開放廣場,面對這個廣場的建築立面皆採取白色,然後置中還有一個噴水池。從廣場到小區入口有一個引水道,噴水池的水可以引到入口處,彷彿是某種精神象徵。哈薩尼是一名成功的移民創業家,他在鹿特丹經營餐廳。哈薩尼也是一個夢想家,他對於拉.米迪的要求非常多:需要有管制的大門、有廣場、有噴水池、有很多裝飾、很多小街道跟大街道。住宅區需要有摩洛哥的文化氣息,但是又要能融入鹿特丹內。在蓋起來之前,哈薩尼曾經找過很多人協助他,包含銀行、社會住宅法人、建商等,但都一直沒有實現。後來的建築師杰倫.格斯特(Jeroen Geurst)協助他實現了夢想,他認為哈薩尼對於裝飾太過要求,但荷蘭建築工人沒有這種傳統。他協助哈薩尼將他的構想轉化成建築外觀的顏色、建築配置、開放空間的形狀跟活動等。他們將細節呈現在窗框、磚造的細部、柱子等等,這些對於荷蘭的一般買家也具有吸引力。
新移民社區可否被規劃?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總結來說,流動率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不同族群之間不能太相同也不能太不同、建築規模及管理組織不能過大、地價不能太貴但也不能低到造成類似貧民窟的印象。牽扯到混居模式的都市重建歷程會相當漫長,阿姆斯特丹各大移民社區從二○○○年初開始了改造,到了二○一四年起西區花園城市才有顯著的改變,其中也因為從二○○八年起荷蘭遭遇到金融危機的打擊,而放慢了重建的速度,因此這樣的改變到現在還是進行式。
二○一七年,曾經於二○一一年拜訪海恩並請教關於住宅改裝及如何整合居民的馬丁及桑德,啟動了黏土城的改造計畫,而且隨後的改造結果還相當的成功。馬丁的「荷蘭曙光公司」及桑德的XVW architectuur建築公司,以及合作的康多威瑟斯創意地產公司共同開發設計的「黏土城住宅」(De Flat Kleiburg)公寓改造案,獲得在歐洲建築界擁有很高榮譽的密斯凡德羅獎(英:Mies van der Rohe Award)。當整個拜默爾區舊現代主義住宅大樓數量的七十%都被拆除後,黏土城被留了下來,本來住宅法人羅奇代爾想找美國西岸的建築師事務所做立面的大幅度改造,試圖吸引一些媒體的注意力,並吸引一些住戶進來居住。無奈二○○八年金融危機後再也沒有這樣的經費,黏土城本來的命運也跟其他的大樓一樣會被拆除。但是後來由馬丁的團隊用一歐元將建築物買下來,雖然土地的費用不計入,但建築物仍需就土地支付七十年的使用費,所以事實上還另外需要約新臺幣兩千萬元,這是一個很誇張的計畫,但是在當時一片低迷的建築市場上,這又是有點合理的計畫,因為反正房子都要被拆。
這棟舊式通廊公寓建築物長大約四百公尺,本來有五百個公寓,總共有十一層樓。建築師們的構思是與其拆掉不成功的貧民窟住宅,不如只做公共空間的低度整建,整個花費大約三千萬歐元(折合新臺幣約一億元)。修復樓梯、電梯等公共空間,將低矮的廊道加高加寬,然後用低價(當時市價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出售黏土城內的住宅單元,並且讓買家可以自由選擇垂直或水平打通內部的單元,以連成較大的新住宅單元,一種類似買家可以DIY大幅度改建混凝土公寓的概念。原本建築物的一樓都是倉儲空間,建築師們將倉儲空間挪到大樓上方不同的地方,將地面層空出來,形成供社區娛樂與交誼的場所。整棟曲折的長條形建築分成四段整修,分別在二○一三、二○一四、二○一五及二○一六年整修完成,並且分階段出售。黏土城在市場上的反應不錯,各式各樣的新型態住戶和年輕人開始住進來。原有的拜默爾居民、遷入的阿姆斯特丹居民以及遷入的非阿姆斯特丹居民各占約三分之一的比例組成。有些住戶帶著幼小的孩子進來看屋,走進破敗的室內,順便來場建築教育,向孩子說明拆除牆壁可以創造空間的流動感,或是水電管線的原理。孩子則興奮地在空曠的公寓內奔跑,感受創造生活的可能性。也有單身的藝術家搬進來,買了三戶原本的住宅單元,將裡面打通後實驗各種創新的生活型態,並且設置了自己的工作室。甚至有摩洛哥家庭買了五個公寓單元,跨越垂直向的三個樓層,組成了一個T字型,在中間垂直挑高的空間還有個小小的伊斯蘭教禮拜堂。
而這樣公民參與都市重建的過程,也成為荷蘭都市及住宅區規劃的新時代典範。我才發現,住商的混合似乎一直都不是荷蘭人重視的重點,而是怎樣建立一個協調性、人群混合,在彼此不互相干擾的狀況下進行合作、可以運作的社會體制,讓國家可以一直向前驅動。
所以與其說是城市機能的混合(譬如在臺灣及部分亞洲城市,對於住商混合的便利性追求),我發現阿姆斯特丹這座城市更加追求不同人群的混合,或是不同社會性的混合。這種混合不一定是要大家住在一起,但是社會性的調和卻是讓大家一起走下去的基礎。在每一階段的共識下,讓城市開發可以在不造成衝突的原則下繼續執行;在每個時代不同經濟條件下,讓建築物興建或是再利用,且能不造成資源的浪費,這似乎是這座城市的日常下,持續在運轉的中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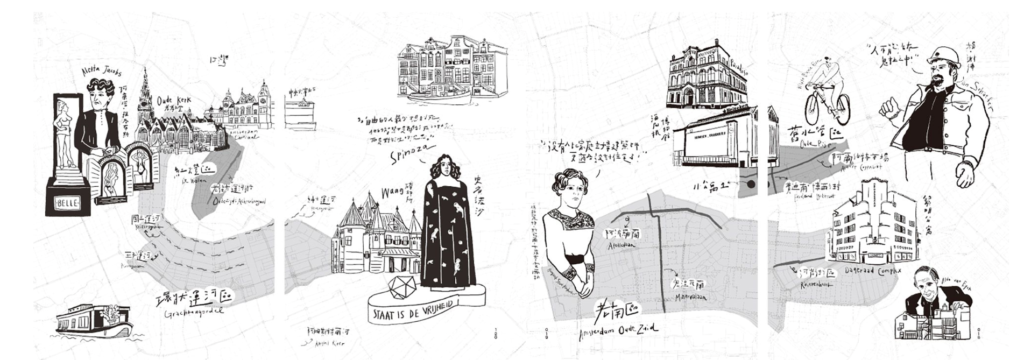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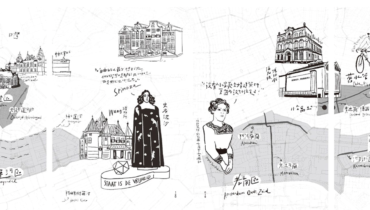
發佈留言